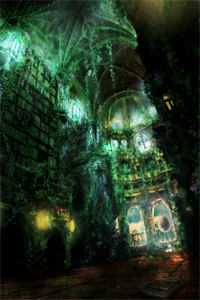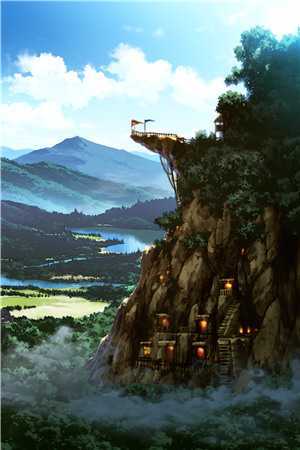牧歌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略群小说luequn.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陈兴旺一高兴总是叫我小子。这小子!又机灵又勤快的,只可惜投错了胎了——他拖着长音把个了字说得很重,这要是出生在一个贫下中农的家庭里头该多好啊!……
在他看来,好像只要家庭出身好就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未来,好的前程似的。而他的意识里,区分家庭好与不好的唯一标准便是家庭成分属不属于贫下中农。我想,这样的认知肯定与他的生活境遇有关。
在物质财富和政治身份的伦理选择上,陈兴旺在精神上是矛盾而分裂的。一方面,他十分明白财富在贫瘠环境中的巨大作用并积极渴望得到财富,因而在为儿子陈传玉求亲时,给田玉英家送去了大金鹿自行车;另一方面,他又为自己拥有标志着政治身份的贫下中农而沾沾自喜,这种价值观的内在矛盾是陈兴旺自己认识不到的。当田玉英的儿子虎娃因病而死,田兴旺痛哭着按照风俗在去掩埋虎娃的路上,有一段特别让人心痛和惊悚的叙述:虎娃似乎知道爷爷将要做什么,所以,那双呆滞不动,但是却依然清澈的眼睛眨都不眨一下,带着还是死去时的纯真和稚气惊愕地望他爷爷和这个世界。陈兴旺的目光碰到这双眼睛时眼睛紧闭了一下。但是一想到他那有羊羔子疯病的疯儿子,及顾先生交代给玉英吃猪肚子的情景,陈兴旺又立马张开了眼睛。陈兴旺一咬牙举起了手中的斧子。(《画里画外》)虎娃名义上是自己的孙子,实际上又是自己的亲生子,此时的陈兴旺内心世界应该说已经完全崩溃。在他自己的伦理选择的结果面前,这一行为呈现了极其复杂的伦理情感。如前所述,他在伦理悖论中选择了伦理禁忌,当他举起斧头砸向虎娃的尸体时,其已经崩溃的精神世界至少存在这样几种可能:一是虎娃的尸体就是陈兴旺违反伦理禁忌的罪证,所以要毁掉他,更重要的是在自己的情感精神中消弭掉这个罪证,来求得一些自我安慰,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二是为自己此前的一系列违反伦理禁忌的行为有了罪感而悔恨不已,对不起自己的儿子陈传玉和儿媳田玉英。三是由崔文清身上和顾先生的话推出吃什么补什么,幻想用死去的虎娃的脑浆治好陈传玉的脑病。或许这三种心理都存在。这仅是文本再现出的情感精神性状,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陈兴旺这一典型人物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农民的深层次的多重性心理性格:懦弱、残暴和愚昧等。这几种心理性格在不同条件下会以不同的方式呈现。陈兴旺如果真的有罪感并有救赎意识,他最应该做的是向他者释放最大的善意,包括让幼小的虎娃入土为安;同时会选择一定的方式让自己的肉体或精神得到现实惩罚。但他不会也不可能做到救赎。
作家在插叙历史片段时,也用了相当篇幅写了诸多人物在一种伦理混沌中生活的情节,这都表明了伦理混沌导致的人的内在情感精神的混沌以至矛盾冲突。如田玉英在出嫁的路上拜一处庙的遗址以求神保佑自己将来的生活,而当年这庙里的住持却是一个色狼,被人弄瞎了双眼。每一个出嫁的、或嫁过来的女孩子都要到这处遗址来叩拜。这颇具讽刺意味的情节,恰恰说明了普遍性的人的情感精神的混沌和虚妄。这也透视出了人在这种伦理混沌中以自己认为非常真诚本质上却虚假地生活着的艰难。而这种虚假,恰如我对罗中立名作《父亲》中分析的那样:
父亲用他那黑洞一样的眼睛直瞪瞪地看着我,强烈阳光下,多皱而挂满了汗珠的古铜一样的脸上泛着亮光。这是一张闰土的脸,阿Q的脸,老通宝的脸;同时也是一张愚公的脸,夸父的脸,彭祖、老子的脸,卖炭翁的脸。这张脸上叠印着华夏世世代代亿万个农民的面孔,也书写着华夏世世代代亿万个父亲的隐忍与坚韧;这张脸的每一道刀刻一般的皱褶里,除了埋藏着他们所历经的苦难、艰辛与世事沧桑,还隐含着土地一样厚实、素朴的良善;他的眼神里充满了希冀和殷殷期盼。也许,他破旧的粗碗里盛的是黄河水,青筋暴起的血管里流的是中华魂,干瘦弯曲脊背上负载着的是华夏民族大厦……。我禁不住浑身一阵颤栗,似乎感觉到了从那张仅剩下一颗牙齿的半张着的嘴里冒出的烟叶味儿,粗重的喘息声,甚至,还有那种我非常熟悉的汗腥气、酸腐味儿……
我的思绪飘向了千里之外—可是,当画里的父亲和现实中的父亲——陈兴旺、田有才等人连接到一起的时候,我波澜壮阔的的心湖不仅立马恢复了平静,而且还有种向下坠落的沉痛。画里的父亲与现实生活中真实具体的父亲——画里画外只隔着一条边框,可在我的脑海里,无论怎样都很难把他们统一起来。我不禁想起批评家们的在拾穗者背后的地平线上,似乎有造反的长矛和
1793
年的断头台那句话,而就在这时,只觉大脑突然灵光一闪,眼前豁然一亮。我激动得心里突突乱跳。我好想打着响指说声OK!但是环顾一下左右,最终又忍住了。我的硕士毕业论文《画里画外——以〈父亲〉为例,罗中立与米勒农民形象比较研究》顺利地通过了答辩。
这一情节,既表达了作家对于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农民伦理精神内涵的深入分析思考,也凸显出这部小说的伦理价值批判精神,极具典型性,更富有普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