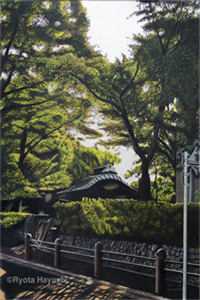第五节 雪域 (第4/6页)
施展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略群小说luequn.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title="从元到清的历史中,安多地区和康巴地区是东亚帝国向雪域输出政治秩序所必经的地理通道。">从长时段来看,这两个地区也构成了雪域与中原得以拥有共享历史记忆的地缘纽带。
吐蕃的崛起依赖于各种历史机缘的耦合,无法复制,在它于842年(唐武宗会昌二年)崩溃之后,<span
class="mark"
title="关于吐蕃的聚与散,其更深层的逻辑详见本书第三章第三节第四小节。">雪域高原无法内生地恢复普遍性的政治秩序,而只能形成一系列很小的区域性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秩序时的关键要素,不是像中原一样比拼哪种组织模式的效率更高,这种比拼要以资源丰富为前提;而是要比拼哪种组织模式的成本更低,这是高原资源稀缺状态所带来的一个根本约束。
在资源稀缺的小共同体中,最低成本的组织模式就是以宗教为核心形成的。各个小共同体的首领同时具有宗教身份,甚至以宗教身份为其首要身份,便可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秩序。雪域高原因此成为古代中国非常独特的一个区域,它成了教权有机会独立于政权之外发展起来的唯一的地方。另一个与此有相似性的地方是中世纪的西欧,世俗秩序崩溃,教权作为更低成本的组织模式,遂获得独立发展的机会,形成庞大的教会。两者的差别在于,西欧的资源匮乏不是地理硬约束所致,政治秩序还有内生性地恢复起来的可能;雪域则没有这个可能,只能等着外部世界以某种方式向其提供政治秩序,雪域则以其宗教性与外部世界形成特定的互动关系,并由此获得自己的历史哲学意义。
倘若政治秩序建立不起来,则雪域无法与外部世界形成有效互动,只能永远在匮乏困窘状态下挣扎;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通过外部世界输入政治秩序,是雪域的内在需求。雪域的秩序输入只能从东亚的帝国方向获得,而无法从印度方向或中亚方向获得,因为这两个方向由于其各自的特定原因,自身也处在一种政治低成熟度的状态,有待通过其他力量输入政治秩序。基于中原帝国与草原帝国的不同治理逻辑,甚至可以说,雪域的政治秩序,只能通过超越于中原、草原之上的普遍帝国才能获得,而这个普遍帝国也将因此真正成就其普遍性。<span
class="mark"
title="关于普遍帝国及其与雪域关系的问题,可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三节第三小节的相关论述。">
由此雪域才获得其完整的精神自觉,它也在这个意义上,与中原、草原、西域、海洋等等各种生态区有着深刻的共享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