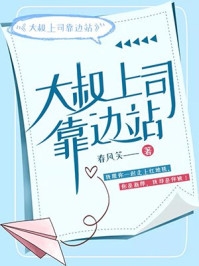第6章 (第1/6页)
爱吃潮汕虾卷的蒙巨兽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略群小说luequn.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珠母海的珍珠,像一粒石子投进砚洲的水潭,激起的涟漪远比沈砚预想的更大。
开采珍珠的队伍分成了两拨:汉人流民负责在浅滩捡拾贝壳,他们手脚麻利,很快就学会了辨认珠母贝的纹路;俚人船户则驾着小船,在黑水沟边缘的暗流里作业,那里的贝壳藏在礁石缝里,往往能取出更大的珍珠。
起初,两拨人还泾渭分明。汉人嫌俚人“不讲规矩”,捡贝壳时把礁石上的海藻都扒光了;俚人笑汉人“怕水”,连齐腰深的地方都不敢去。但当第一批珍珠换来的铁锭运到砚洲时,所有的隔阂都被熔进了铁匠铺的火炉里。
王伯带着几个流民铁匠,用这些铁打了二十把环首刀,刀柄缠着越布,既结实又防滑。他把第一把刀递给了老桨的儿子阿桨——那孩子在雾战中用硬木枪捅穿了三个郡兵的喉咙,却因为枪杆断裂差点送命。
“拿着,”王伯把刀塞进阿桨手里,粗粝的手掌拍了拍他的肩膀,“这刀比你爹的鱼叉厉害,别丢了你爹的脸。”
阿桨握着刀,指腹摩挲着光滑的越布刀柄,突然“扑通”跪在王伯面前,磕了个响头。这是汉人的礼节,他从船上的流民那里学的。王伯愣了愣,眼眶突然红了,赶紧把他扶起来,嘴里骂着“小兔崽子,没大没小”,手却在发抖。
沈砚站在译经坊的废墟边,看着这一幕,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暖了暖。张老夫子正在废墟上搭新的竹棚,他说要建一座“海学”,教汉人和俚人都能看懂的字——用汉字写俚语的发音,用贝纹画中原的星宿。
“子墨,你来看这个。”张老夫子递给他一卷竹简,上面是用朱砂写的字,旁边画着对应的贝纹,“‘潮’字,对应浪花纹;‘船’字,对应舟神图腾。这样,不管是汉人还是俚人,都能认得了。”
沈砚接过竹简,指尖划过那些朱红的笔画。他想起祖父的梵文残卷,突然明白,文字从来不是隔阂,反倒是桥梁——关键在于,有没有人愿意搭这座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