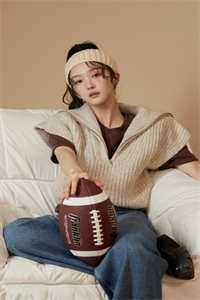牧歌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略群小说luequn.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我到现在还记得,那天是一九七九年的十二月二十八日,农历的腊月初十。那一天,北京城的天空还飘着零星的雪花。我裹着一件黄军用大衣站在天安门广场照了张以天安门城楼为背景的全身像,这张照片后来还被王晓红拿去照相馆放大制作成了镜框,挂在我们家餐桌上方的墙上。当然,现在这镜框早已不知弄到哪里去了。
记得照完相,我在天安门广场附近上的公共汽车,车上的人很拥挤;还记得我抬脚刚要向车厢深处走去的时候,正巧赶上汽车启动加速,我一脚踏空踩了别人的脚,被一个穿面包服、戴蛤蟆镜的家伙推了一把,头撞到了一个女人的柔软的怀里又被女人一迭声骂了好几句乡巴佬,臭流氓!。我一路脸如炙烤,直到下车以后才敢抬起头来。
中国美术馆的展厅里人头攒动,春意盎然,展墙上琳琅满目的作品似乎在向人们传递着振奋人心的信息。我忽觉眼前一亮,欣喜地发现:许多的画家已经开始走出思想的藩篱。
但我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是在哪一个展室,我被一幅高达2米多的巨幅油画攫住了目光。我先是被油画前拥聚的很多人所吸引。他们中,有手拿着照相机的,有拿着速写本记录的,有仰着头凝视观望的,也有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的。他们一个个表情凝重,眼含泪花。想必他们被眼前的画面所深深震撼
我带着疑问向人群走去……
是的。我的心也为之一震。这幅巨幅油画画的是一位大巴山区的农民。他头上包裹着旧得有些泛黄的白布头巾,黝黑、干瘦的脸上青筋暴凸、皱纹密布;高高突起的眉弓,幽深、黯淡的眼睛,空洞、迷茫却又满含着和善和希望的眼神……背景是板实厚重的黄土地一样的明黄色底色。
我待众人离去后趋前几步看了一下标注,是四川美院罗中立的《父亲》。
父亲的脸几乎占据了整幅画面的全部,脸上的皮肤像他用犁铧刚刚深耕过的土地;他惊愕地半张着嘴,嘴唇干裂、苍白,枯树皮一样粗糙的大手端着半碗茶水。这是繁忙、沉重的劳作间隙中的因为太过劳累和焦渴而不得不有的短暂停歇。所以,他的脸上挂满了晶莹剔透的汗珠,藏满污垢的手指头紧扒着破瓷碗的碗沿,皴裂(或受过伤)的右手食指还残留着胶布的印痕。